1
1979年9月,23歲的河北大學化學系畢業生宋志平,被分配到國家建材局直屬的北京新型建築材料試驗廠岩棉車間,任技術員。從那時起,他在建材行業幹了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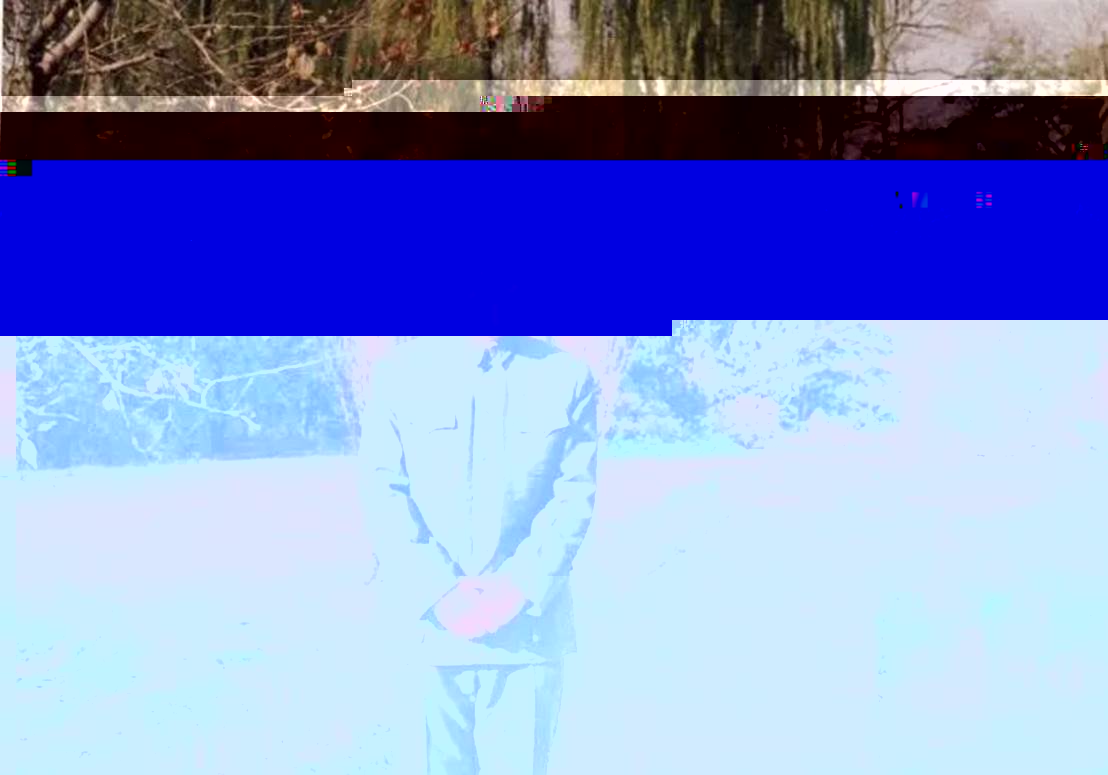
1980年5月,宋志平被選派出國,到瑞典、南斯拉夫等地學習。在沃爾沃公司,他看到了繼電器邏輯控制、伺服馬達執行的“自動化”體系,看到了開放式的大辦公室,每個辦公桌上都有一台大電腦,立體備件倉庫都用電腦控制。“太先進了!”他很震驚。瑞典人過來安慰他:“宋先生,我們60年代買牛奶也是排隊的,隻要你們按改革開放的思路好好幹,不久就會像我們一樣。”
北新建材引進了國外先進設備,但産品賣不掉,大量庫存。因為當時水泥、玻璃、建築陶瓷是通過計劃銷售的,而北新建材生産的是新産品,如石膏闆、岩棉,沒有列入國家計劃,不得不自己去找市場,比如聽說岩棉保溫産品在石化企業和造船廠能用到,就去那裡推銷。
1983年,宋志平開始當推銷員,一幹就是10年,最後做到管銷售的副廠長。為了在全國推銷岩棉、石膏闆,他主持搞了聯營銷售公司,開始是在深圳、上海,後來在全國30多個城市成立了聯營公司,選擇有銷售實力、有倉庫、有商鋪的合作方,合作方有國有的、集體的、外資的、個體的,形成了一張網絡。在這個過程中,宋志平體會到,做企業一定要與人分利,才能把市場做大。
八十年代中期,北新建材的石膏闆等新型材料,從北京用火車運到深圳、廣州、廈門等用量較大的城市,市場從南向北鋪開。1983年的深圳還像一個小縣城,但有很多工地,朝氣蓬勃。宋志平後來回憶說:“北新建材進入市場,最初也是被迫的,後來放開物價,很多企業不适應,但我們很适應,因為我們從來沒有享受過‘計劃’帶來的好處,沒有吃過偏飯。同時,由于北新建材和開放前沿城市的市場聯系在一起,幹部經常跑那裡,對他們也産生了市場化的影響。”
雖然銷售不錯,但生産又出了問題。石膏闆生産線的設計産能是一年2000萬平方米,實際隻能産出600到700萬平方米。最初以為是德國設備商的問題,後來發現不是設備問題,是職工積極性不高,操作出了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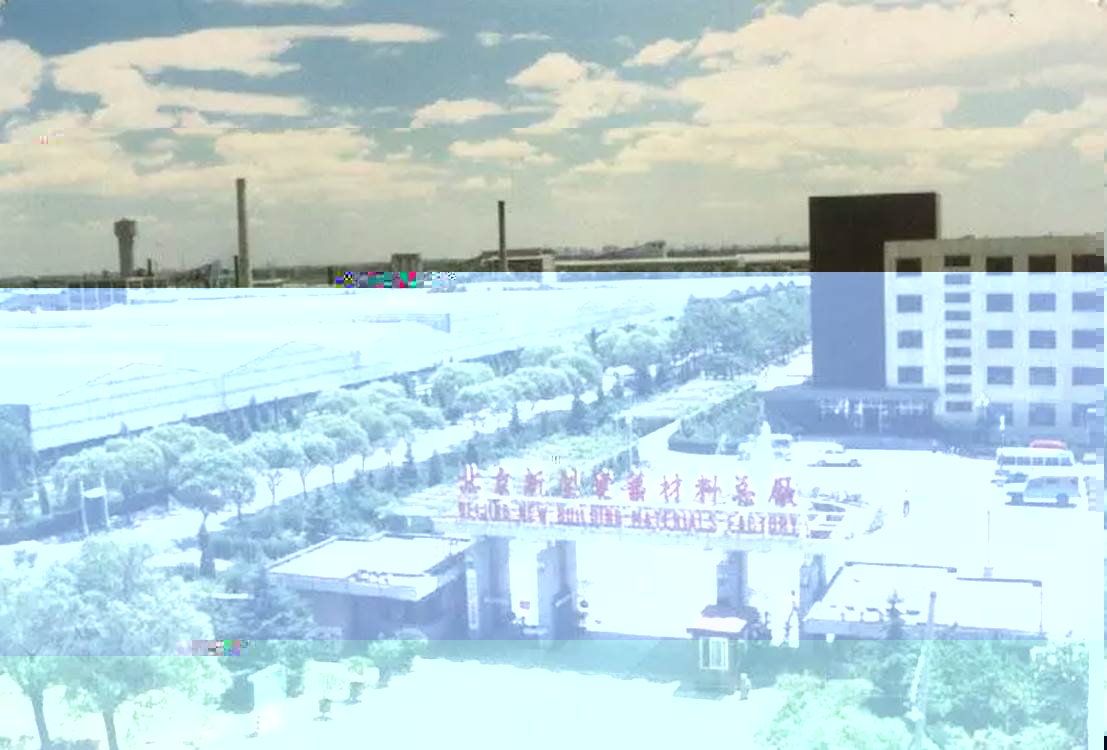
1993年初,宋志平被任命為廠長。這時廠裡機制老化,資金匮乏,人心渙散,春節後上班第一天,宋志平站在廠門口數遲到人數,多達280多人!他每天第一個到工廠記錄出勤,6天後,遲到人數變為0。
當時國企已經實施了“撥改貸”,即由财政無償撥款改為通過銀行以貸款方式提供流動資金,但北新建材的信用等級不夠,銀行拒絕貸款。面對困境,宋志平帶頭和全體員工一起集資,短短幾個月募集到400萬元,買了原材料,企業得以正常運轉,當年就生産了1300萬平方米的石膏闆,一年後歸還了所有集資款。
管理就要以身作則。有一次,出口到韓國的岩棉闆上面有一個腳印,韓國人要求退貨。宋志平自罰500元,接着主管生産廠長、車間主任也都罰了,他還寫了一個“罪己诏”。他說:“罰自己一次款,比訓别人一萬次都強。做企業領導人,不能把責任全歸到工人身上。”他每天下午3點左右到各個車間裡看,夜裡12點左右再去一次,讓幹部和員工知道他與他們同在。他的作風感染了員工,他還承諾給大家“工資年年漲,房子年年蓋”,而且都做到了。2001年北京市表彰優秀企業家,用優惠價獎勵宋志平一套在萬柳的200平方米的房子,他和愛人商量後,把房子改成兩套100平方米的,獎勵給了廠裡的兩名創新有功的技術人員,以此诠釋創新有功當獎的理念。

1994年,國家遴選出100家國企推進試點,探索建立“産權清晰、權責明确、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國家建材局旗下隻有一家被選中,就是北新建材。1997年,北新建材成功上市,募集了2.57億元。
對于上市,宋志平曾說,上市妙不可言,也苦不堪言。“妙不可言”是指通過上市解決了當時正在建設的石膏闆二線和礦棉吸音闆生産線所需的資金,“苦不堪言”是指上市後企業的重要信息、發展情況,市場一覽無餘,股民情緒跟企業業績挂鈎,做得好他用手投票,做得不好他用腳投票。

事實上,北新建材上市後有一段時間非常困難,主要是因為外資企業紛紛在中國投資建廠,一些小生産線也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石膏闆價格從每平方米12.28元一直降到6塊多錢,股價下跌,股民一片責備之聲。那段日子,宋志平常常整夜失眠,導緻眼睛晶體出水,毛細血管破裂,視力嚴重下降,他愛人是醫生,每天晚上都要在家裡給他打一針。但由于堅持“一切服從于市場”的理念,為客戶提供“超值服務”,特别是北新建材的石膏闆強度高,而外企的石膏闆由于闆芯不實,握釘力不強,施工方不喜歡,在殘酷的競争中,北新建材終于擴大了優勢,而外企的生意越來越差,有的還撤出了市場。
2000年前後,北新建材進入了健康發展的快車道,很快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石膏闆産業集團。
2
2002年初,北新建材的母公司中國新型建材集團(簡稱“中新集團”)遇到嚴重困難,宋志平臨危受命,出任總經理。第一次與職工見面,他發表就職演說,辦公室主任跑來遞給他一張銀行凍結集團财産通知書。當時中新集團年銷售收入20億元,負債32億元。他的前任總經理給他打了個電話:“志平我從彈坑裡爬出來了,該你進去了!”
中新集團的問題不隻是逾期債務多,沒有信用等級,融不到資,集團辦公樓被查封,院子裡不敢放汽車,稍有不慎就會被法院扣押,最大的問題是除了北新建材之外沒有像樣的企業,壁紙廠、塗料廠等在市場上都失敗了,很多員工都在議論下個月還會不會發工資。
對一家在充分競争領域的央企而言,除了在市場上找食,别無他途。宋志平說:“我們沒有含上金鑰匙,也沒有捧着金飯碗,隻有扔掉僥幸心理,堅定改革,才能新生。”
他首先跑到一家家銀行和資産公司,尋求債務重組,“楊白勞”主動見“黃世仁”,最後和最大的債主信達資産管理公司進行了大規模的債務重組,可以輕裝上陣了。更重要的,他一直在思考中新集團接下來究竟要幹什麼。2002年7月,在北京龍都飯店召開的戰略研讨會上,建材系統的老同志異口同聲,中新集團想成為行業裡的“一号”,做大做強,必須做水泥。

當時,中新集團按照國家經貿委承債式兼并的要求,收了幾家水泥廠,但規模無法與海螺、冀東這些大企業比,更像一群“烏合之衆”,宋志平自己也不懂水泥。但他看到了城市化的前景,看到水泥正處在從小立窯向新型幹法轉化的機遇,而水泥占建材行業GDP的70%,于是決定從普通裝飾材料的制造業退出,在水泥這樣的大産業生根,同時帶動新型建材等發展。2003年4月16日,中新集團正式更名為中國建築材料集團(簡稱中國建材),表明了做大主流建材的決心。
2003年6月,宋志平到旗下的魯南水泥考察,聽彙報時反複問效益情況,但沒人跟他說,後來得知企業虧損。他說:“做企業效益回避不了,你們說全省都在學魯南,但魯南不賺錢,學什麼?”當時集團很多幹部都沒有盈利概念,宋志平專門開過一個會,告訴大家做企業最重要的就是賺錢,企業一把手首先是經營者,經營的目标就是賺錢,不會經營的企業領導者不稱職。
在進入水泥的過程中,宋志平開始進行後來被稱為“央企市營”的一整套改革,即植根“央企”的屬性,進行股份多元化、規範的公司制和法人治理結構、職業經理人制度、内部市場化機制、外部市場化運營五個方面的變革。2006年3月,中國建材股份公司在香港H股上市,募集資金21億港元。之後,宋志平開始用收購重組的辦法進行水泥行業的整合。
2006年7月,中國建材收購了徐州海螺水泥。當時中國建材在徐州有一個巨龍水泥,有2條生産線,其中有一條日産水泥5000噸,徐州的水泥都由巨龍供應。後來海螺水泥進入,它有員工持股,做了條日産1萬噸的大型生産線。雙方陷入苦戰和惡性殺價,最後都出現了虧損。對海螺來講,這是一條線的問題,對中國建材來說,則關系到水泥事業到底能否做下去。宋志平認為,必須把徐州海螺收了,否則不可能在水泥市場立足。最後耗費了人民币9.61億元,并為徐州海螺的2.3億元銀行借款作擔保,收購了徐州海螺全部股權。收購後,每噸水泥價格就恢複性地提高了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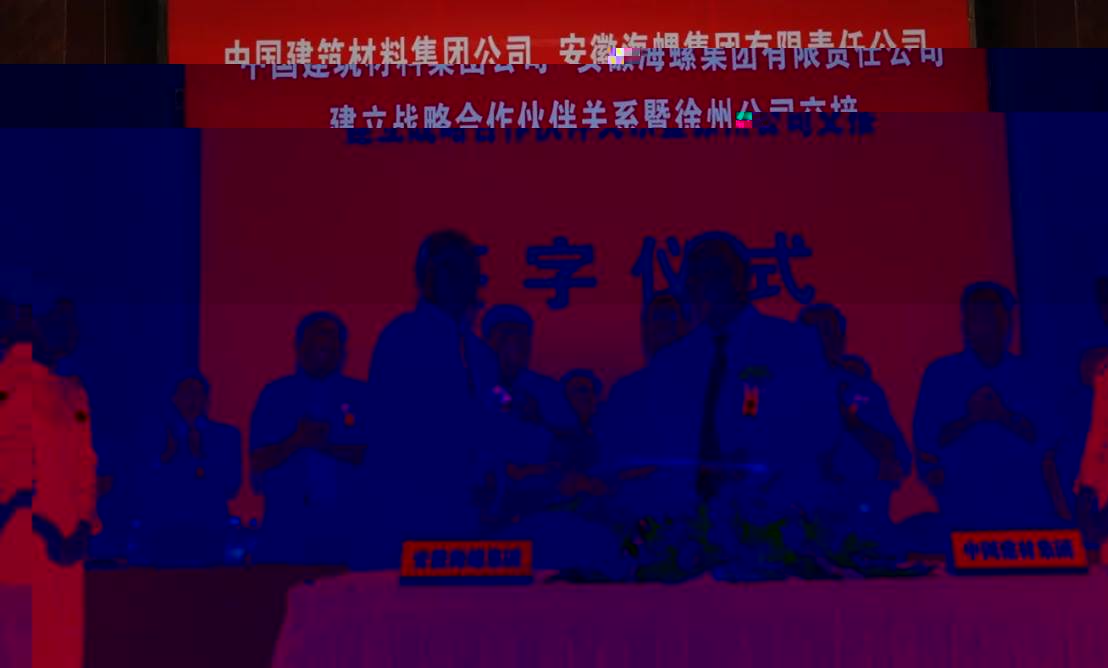
最重要的收購發生在浙江,中國建材在浙江沒有一點水泥産能,當地水泥企業打價格戰,價格從每噸400多元一路跌至一兩百元。2007年4月,宋志平在杭州汪莊飯店請浙江水泥、三獅水泥、虎山水泥、尖峰水泥四家企業的老總喝茶,他們占浙江市場的半壁江山。從早晨喝到晚上,宋志平提出了央企與民營資本合作的“三原則”:
一是價格公允,不強買強賣,一律請中介機構評估;
二是民營企業保留30%股權,“以前你是100%,可是你打惡仗,人人虧損。我和你合作,雖然你隻留下30%股份,但現在就能拿到很多錢,今後還會分到很多錢。與其100%老賠錢,不如30%賺點錢。”
三是企業經營管理層全部留下,大家繼續做企業的CEO。
最終,四位民企掌門人接受了重組方案。
随後一年多,中國建材集團在南方六省一市展開了對大大小小900多家水泥企業的重組,這就是南方水泥。到2011年,又完成了對西南地區1億多噸水泥産能的整合,最終成為全球水泥行業龍頭企業。
宋志平不隻是一個擴張主義者,他有所為有所不為。水泥是個短腿産品,合理的經濟運輸半徑最多隻有200多公裡。中國建材集中精力做淮海、南方、西南和東北區域,深耕市場,但不在安徽做,因為有海螺;不在京津冀做,因為有冀東;不在湖北做,因為有華新;河南隻在南陽和洛陽做了一塊,與天瑞水泥和同力水泥三足鼎立。在所到區域,則強調核心利潤區,在核心利潤區裡要能控盤,有一定的定價實力和定價權,如果不能控盤就放棄,如北方水泥就是坐擁黑龍江,在吉林與亞泰平分天下,而在遼甯隻做大連市場。
宋志平不僅重視戰略,而且注重精細化管理。收購徐州海螺當天,他和做了一輩子水泥,當時的海螺董事長郭文叁在徐州開元賓館旁的湖邊散步,郭文叁對他說,其實水泥廠不難管理,關鍵是做好兩件事:一件是管理好中控室的操作員,每個月工廠内部對标,進行末位淘汰;一件是工廠之間對标,噸煤耗、噸電耗、噸油耗、噸球耗、噸耐火磚耗、噸修理費等各項成本指标要持續對标。收購徐州海螺3個月後,宋志平就在徐州召開績效管理現場會,提出了一體化、模式化、制度化、流程化和數字化的“五化”管理模式,後來又擴展了銷售集中、采購集中、财務集中、投資決策集中、技術集中的“五個集中”,以及淨利潤、産品價格、成本費用、現金流、資産負債率的“五個關鍵指标”。
3
1999年4月22日,中國化建(600176,SH)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上市指标是中新集團獲得的,但它缺乏好的資産,于是作為主發起人和另外幾家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位于浙江桐鄉的民企、玻纖生産企業巨石集團的經營性資産注入了中國化建。中國化建後來更名為中國玻纖,再更名為中國巨石,今天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競争力最強的玻璃纖維企業。中國建材集團是第一大股東,最早創立巨石的振石控股集團是第二大股東。

今年4月22日,我參加了中國巨石上市20周年主題論壇,和宋志平、中國巨石總裁張毓強、桐鄉市市長于會遊進行了交流。中國巨石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個樣闆,其經驗彌足珍貴。
上市很風光,但央企和民企接觸的初期,都還是有顧慮的。張毓強是民企出身,擔心多年的市場化的文化和決策機制會被國資的管控模式所抑制,而且中國化建成立時,為确保控股權,将不少總資産規模大、但盈利能力不強的業務放在上市公司裡,巨石集團以占中國化建總資産的30%,創造了90%以上的營業收入和淨利潤,貢獻和股權比例不匹配。而在中新集團,也有人說,“我們有上市指标,很多人搶着要,為什麼要與民企合作?這不是屈尊嗎?”
中國巨石能成功走到今天,用張毓強的話,“雖然中國建材集團是國企,但從事的是充分競争的行業,産品是市場化的,決策層的思維也是市場化的。”他說,當初巨石缺乏資金,發展受到嚴重制約,如果不是和央企混改上市,而是一步一步自己做,做成世界第一可能要200年。雖然混合之後,不是第一大股東了,但能按照市場化、專業化的方向充分施展,做到世界第一,這是最大的财富。
2002年宋志平出任中新集團總經理後,派曹江林出任中國化建的董事長,和張毓強形成組合。曹江林推動了一系列改革,在完善内部監管機制的基礎上,明确了作為大股東的中新集團和巨石集團的各自定位:中新集團實施戰略管控,隻掌控投資、布局、财務和合規經營等重大事項,對巨石集團具體的經營管理、用人不插手,給予企業在法律法規允許範圍内最大的自主權;完善治理制度,重視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的有效運作加強對企業的法治化管理,作為大股東根據公司章程、董事會議事規則、總經理工作細則等制度,對投資、融資、關聯交易等重大事項的決策履行程序。管理層、董事會、股東大會三個層次都有明确的職責和權限,國資和民營均照章辦事。
在宋志平和曹江林的推動下,中國化建和巨石集團的關系逐步理順,為巨石接下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治理基礎。中國化建将不良資産及虧損資産剝離,明确将玻璃纖維作為業務戰略方向,主要由巨石集團進行運營。在巨石集團需要支持的時候,中新集團(中國建材集團)全力支持。

宋志平說,做企業關鍵是要選對一個業務和一個企業家,選對一個企業家最不容易,對的企業家可遇不可求。他認為巨石集團的創始人張毓強就是那種以廠為家、做企業的癡迷者,多年來他都是早晨6點起床去工廠,先跑步,從在食堂吃早餐起就開會,晚上很晚才離開。宋志平回顧了這樣一段故事:
“在巨石發展中,桐鄉市政府給予了大力支持。随着地方經濟的發展,市裡提出能否把上市公司總部從北京搬至桐鄉。巨石總部搬到桐鄉有合理的地方,全世界的産業集團總部往往設在一些中小城市,況且從長期看,上市公司總部的幾十号人身在北京、遠離生産基地也不是辦法。但是,我擔心桐鄉的融資環境不夠好。又過了兩年,随着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融資不再是問題。于是,2014年金秋十月,我們正式把巨石總部遷至桐鄉。這讓桐鄉市政府很感動,又給了巨石不少支持。除了上市公司總部遷址外,公司管理層還建議把公司名字從‘中國玻纖’改為‘中國巨石’,但由于‘中國玻纖’最初是我起的名字,所以沒人敢對我說。我知道這件事後,考慮到中國玻纖的産品商标是‘巨石’牌,而且是著名品牌,企業的名字和品牌一緻又是大多數企業的做法,所以我同意更名,并于2015年去桐鄉參加了更名授牌儀式。對中國巨石的遷址和更名,無論地方政府、行業還是在市場上,都産生了良好反響,大家認為中國建材這種尊重市場和做事包容的文化難能可貴。”
混改在中國并不是新生事物,但長期以來,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宋志平是真心按照市場規律進行混改的,他對我說:“把一個央企是第一大股東的上市公司的總部從首都遷到一個縣級市,我也有顧慮,但我想,到底是做一個大廟裡被邊緣化的小神仙,還是做一個小廟裡的大神仙,肯定後者更利于企業的發展。”他還讓中國建材集團到中國巨石深度調研,編撰了《增節降工作法》,在全集團推廣,把民企的活力在更大範圍内發揚。
4月22日,張毓強對參加論壇的全體與會者說:“有宋總這樣的領導,我們對混改無怨無悔。”
4
2009年4月的一天,宋志平接到國資委的電話,讓他去一趟。到了才知道,上級要他出任國藥集團董事長。
國藥的發展模式複制了中國建材“央企市營”的做法,與民企進行混改,建立銷售網絡。2009年9月23日,國藥控股在香港聯交所挂牌上市,募集60多億港元,之後通過聯合重組在全國建立起龐大的醫藥健康産業平台。
2013年,國藥集團與中國建材集團一同進入《财富》雜志評選的“世界500強企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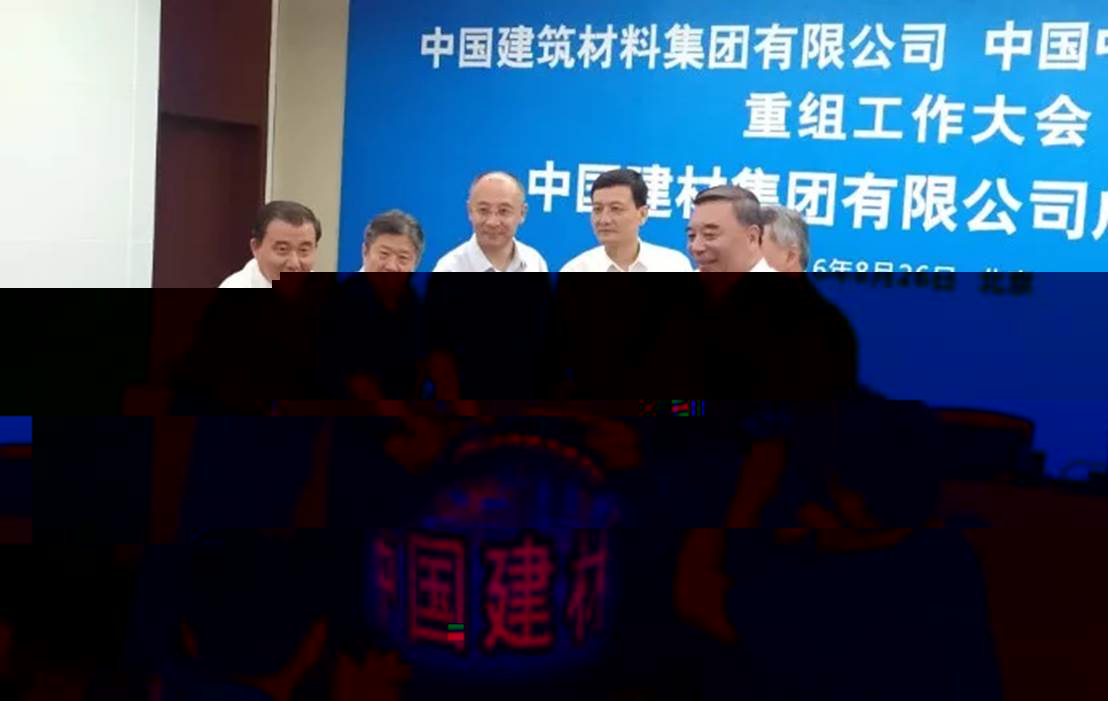
2014年,宋志平主動請辭離開國藥集團。為增強中國建材的國際競争力,他又推進了中國建材與另外一家央企中材集團的合并重組。2016年8月,“兩材重組”正式獲得國務院批準,中國建材與中材集團合并組成新的中國建材集團。2018年5月3日,新中國建材H股正式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交易。重組後的新集團在水泥、商品混凝土、石膏闆、玻璃纖維、風電葉片以及國際水泥工程和餘熱發電工程市場六個領域位居世界第一。近十年來,他們還為國外建造了300多條水泥生産線和近60條玻璃生産線,都是世界一流的技術裝備,市場占有率高達65%。
如同張瑞敏的“人單合一”模式一樣,宋志平開創的“央企市營”——以市場為導向,通過資本手段整合資源做大,充分依靠企業家精神參與競争,提高技術素質和管理水平做強做優——也引起了國際管理學界的濃厚興趣。哈佛大學伟德客户端做中國建材的重組案例時,就把這個詞收了進去。因為是自創,翻譯想了半天譯為“Marketize SOE”,即“市場化了的國企”。
關于國企,已經改了幾十年,也争了幾十年。宋志平的觀點是通過混改實現“國民共進”,他說中國建材的國有資本隻占25%,社會資本、非公資本、股民資本占75%,已經不是傳統的國企。“能夠救國企的是市場改革,如果沒有市場改革,不管建材也好,不管國藥也好,這些企業可能都不存在了。”
宋志平推崇“第三隻手”,既不是完全的無形的手,也不是政府的手,而是有競争力和創新能力的大企業之手,“大企業在市場進行一定的整合,形成幾個大企業之間的良性競争,解決無序性的問題。”以水泥行業為例,中國建材重組水泥之前,行業前十家企業加在一起,在整個行業的集中度是9%,而西方是80%,中國建材重組水泥後,行業的集中度是63%。中國建材重組前,水泥行業的利潤一年是80億元,2018年水泥行業的利潤是1546億元,這筆利潤,國資有份,民資有份,股民有份。“就像一杯茶水,一加一大于二,可能水是國企,茶葉是民企,但混成一杯茶水喝下去,還要區分嗎?可以互相融合,可以交叉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好像太極圖中的白魚和黑魚。”
“混合所有制不光引入了資金和市場機制,還有利于監管,”宋志平說,“我在國藥集團和中國建材的體會是,凡是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的企業,往往出問題的就少,單一管理的體制出的問題更多。”
國有經濟與市場結合是一個世界難題,曾有位老領導說,“如果誰能解決中國國企的問題,誰就是當代的馬克思”。宋志平說,我是個實踐主義者,相信實踐出真知,改革開放40年,國企改革雖然尚未完成,但已經破題了。就是出資人管資本,不要具體管企業,比如水泥企業怎麼搞,需要做的是把資本放入國家出資的投資公司(如中國建材),投資公司投下去的是股本,股本可多可少、可進可退,在混合所有制企業裡用股權說話,和任何股東是一樣的權利,這樣也能落實競争中性了。“在競争領域,如果是國家納稅人全資投的企業,和納稅者私人辦的企業進行競争,肯定是悖論。但如果國家投資公司投的股本,放到企業裡一點,而且是流動的,市場是能接受的。混合所有制還解決了國企長期政企不分的問題和機制的問題,如果是百分之百的國企,怎麼和政府分開?”
“有人認為國企不用改革照樣可以搞好,但回顧自己40年來搞企業的經曆,我可以明确地說,沒有改革就沒有國企的今天。我并非天生喜歡改革。改革意味着變化,意味着利益再分配,往往伴随着傷痛和眼淚。那為什麼還要改革呢?我覺得,這一切源于責任,我們有責任解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項難題,而改革正是奔着解決問題展開的,既然重任在肩,既然别無選擇,我們就必須一次次勇敢地邁步,哪怕前方荊棘密布也要一路向前,永不回頭。”宋志平說。
5
在這篇文章中,我沒有讨論國企應該如何進行戰略性調整、為民企留出更大空間的問題(根據有關領導講話,國民經濟398個行業,380個行業中有國企),沒有讨論如何在實踐中消除對國企和民企的差别對待的問題,沒有讨論盡管國企獲得的研發補貼與銷售額之占比遠高于民企,但民企的專利授予量一直顯著高于國企的問題,也沒有讨論過去一兩年國企利潤的顯著增加,與其更多處于上遊生産資料領域的地位的關系(2018年原材料工業實現利潤近2萬億元,占整個工業利潤的29.8%)……,所有這些問題都說明,深化國企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必須快走,國企改革是整個經濟改革繞不過去、必須攻克的關。
這篇文章聚焦的是,在給定的資源配置條件下,中國的國企能不能通過改革成為市場化、國際化、現代化的競争主體,展現出内生的動力和創新的活力,向世界一流企業邁進?
宋志平領導的中國建材集團的改革成就,給了我确定的答案。
在中國建材集團,有着世界一流企業抱負的企業不是一家兩家,是一批,這些企業背後都有追求卓越、永不滿足的企業家。當我走向他們,一開始也是充滿疑問的,為什麼我們做不出3M那樣的高性能膠水?為什麼中國的大飛機不用中國的碳纖維?我們的材料能用在飛機發動機上嗎?他們讓我明白,中國人在高性能纖維、先進複合材料、高分子膜材料、光電玻璃、特種功能玻璃、高端工業陶瓷、石墨基碳材料、人工晶體材料等新材料方面已經有了很多突破,他們的産品已經應用于載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項目,很快也會用在大飛機和飛機發動機上面。
“你要相信像中國建材這樣的企業,我們有26家國家級的科研設計院所,有幾萬名科技研發人員,有的材料研究了40年才突破,很多創新是長期積累的結果。”中國建材集團副董事長李新華對我說。
這個“草根央企”的改革曆程,深深感染了我。
2018年全國的國有資産有178.7萬億元,國有權益總額為63.1萬億元;全國的國有金融企業資産有241萬億元,國有權益為16.2萬億元(注:金融資産為2017年數字)。中化集團董事長甯高甯說,如果國有企業的ROA(資産收益率)能增加1個百分點的回報,就是1.78萬億元。
2018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18.34萬億元,國企的資産收益率增加1%,等于全國财政收入增加10%。甯高甯說,這樣的話,減稅、建醫院、學校,增加教育經費,等等,就沒問題了。
毫無疑問,這需要國企、央企的進一步改革,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和公平競争原則,加快實現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化,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讓市場化原則和企業家精神真正融入國企、央企的肌體。
宋志平說:“央企100多家企業,隻有十家左右有自然壟斷成分,絕大多數都在充分競争領域裡,所以能發展壯大,并不是靠大家所想象的壟斷,也不是靠一些人講的堅守過去那些傳統的管理方法。誰先改革誰就能活下來,誰能改得徹底誰能夠成功,哪裡有更充沛的企業家精神哪裡就更有活力。”
尊重市場,尊重規律,勇于競争,善于競争,創新機制,弘揚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勞模精神和全員參與的精神。大道至簡,道理并不複雜。
來源:微信公衆号“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