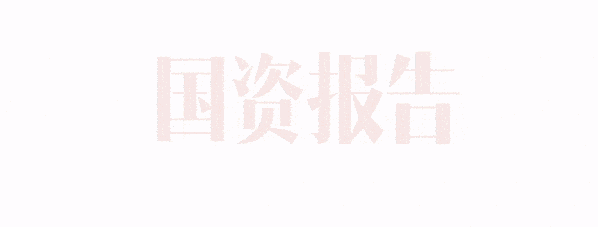
文 · 國資報告記者 王倩倩
原載國資報告雜志18年第3期
201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印發實施《關于建立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産管理情況制度的意見》(下稱《意見》)。作為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的首份文件,2018年伊始,國資監管體制改革向前邁出重要步伐。
國有資産歸屬全民所有,理應由全國人大行使監督職權。近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多次就國有資産管理聽取國務院專項工作報告,人大國有資産監督職能有所增強。然而,管好用好規模龐大的國有資産,亟待實現人大監督職能的制度化、規範化。切實摸清國有資産家底,算清國有資産“明白賬”,築牢國有資産安全防線,成為《意見》出台的出發點。
“建立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産監管的制度,加強人大監督職能具有深遠影響,将掀開中國模式嶄新一頁。”伟德客户端院長劉紀鵬接受《國資報告》專訪時表示。在他看來,實現國有資本和市場經濟創新結合的國資監管體制是中國模式的靈魂。規範國資監管體制要治本,應實現科學分工、明确架構、責權一緻,方可公開透明、全覆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圍繞“加強人大國有資産監督職能”完善國資監管體制,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向國資監管過程中長期存在的責任主體、監督主體缺位、錯位等問題,舉起了改革的“手術刀”。
以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牽頭,财政部、國務院國資委參與承擔“建立國務院向全面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産管理情況的制度”的改革任務,《意見》的出台使得國資監管體制進一步明确、清晰。
就報告主體而言,按照《意見》要求,“國務院每年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産管理情況,依法由國務院負責同志進行報告,也可以委托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報告。”
對于這一制度化規定,劉紀鵬表示,“以往每年隻有‘一府兩院’(指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向人大進行專項工作報告,由财政部提交财政預算報告,并未正式将聽取國有資産管理情況報告納入法定程序。此項改革,具有戰略意義。”
從報告具體内容來看,《意見》列出七大方面的重點,如總體資産負債,國有資本投向、布局和風險控制,國有企業改革,國有資産監管,國有資産處置和收益分配,境外投資形成的資産,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等。
對此,劉紀鵬說,“《意見》對國資管理工作要點進一步具體、細化,并且列入法律和制度中,有利于提高國有資産管理公開透明度,提升國有資産管理公信力,推動規範和改進國有資産管理。”
如何為報告制定一套嚴格的審議程序,事關監督成效。《意見》中,國有資産管理情況報告的提交節點、審議方式、整改、問責等相關内容作出說明。值得一提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于貫徹落實黨中央有關國有資産重大決策部署和方針政策情況,完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落實黨中央有關國有資産和國有企業改革方案情況等九大審議重點,構築起全方位監督的基石。
“一套完整的審議程序,使得國有資産管理部門有了壓力、有了具體職責、有了明确監管問責的上級。由全國人大過問情況、聽取彙報,完善功能、更加務實。國有資産管理部門的法律屬性、行政管理程序屬性終于開始朝着理順的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劉紀鵬說。
建立健全人大國有資産報告監督機制,預算是龍頭。《意見》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和審議國務院關于國有資産管理情況報告工作,要與預算決算審查監督緊密銜接,特别是要與對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決算、部門預算決算審查監督相結合。”
對于建立這一機制的初衷,劉紀鵬表示:“錢從哪兒來到哪去?花的怎麼樣?有沒有流失?報告的重點就是預算這點事。”在他看來,今後應該明确國有資産管理部門就向全國人大預算工作委員會負責,如果涉及改革、國有資本布局等方面,預算部門應和其他部門共同配合。
改革的亮點不容忽視,但面對《意見》所要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國資監管體制改革仍存一些挑戰。
值得強調的是,近年來,國務院不斷加強國有資産管理,國有資産産權日益明晰,國有資産管理機制逐步理順,會計統計等基礎工作顯著加強,國有資産管理取得了諸多積極進展。
然而,問題的存在無法回避。
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就《意見》答記者問時提到,此前報告的主要是國務院國資委管理的企業國有資産管理情況,還沒有完全覆蓋其他企業國有資産,特别是金融企業國有資産。
如《意見》所言,“堅持問題導向,應着力解決國有資産底數不夠清楚、管理不夠公開透明、人大監督所需信息不夠充分和監督不夠有力等突出問題。”
為科學、準确、及時掌握境内外國有資産基本情況,《意見》要求“國務院關于國有資産管理情況的年度報告采取綜合報告和專項報告相結合的方式。綜合報告全面反映各類國有資産基本情況,專項報告分别反映企業國有資産(不含金融企業)、金融企業國有資産、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産、國有自然資源等國有資産管理情況。各類國有資産報告要彙總反映全國情況。”
既有綜合報告,也有專項報告,切實摸清家底已然成為全國人大完善監督職能的基礎。但分類施策能否解決監管問題之本,劉紀鵬給出了自己的意見。
“事實上,金融企業、企業(不含金融企業)、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産等,都不同程度存在公開透明等問題。政府部門不能隻要權利,不要責任。完善人大監督體制要治本,根本上要科學分工、責權利一緻。”他告訴記者。
以統計經營性國有資産底數為例,劉紀鵬向《國資報告》記者分析,“無論是從産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相結合的趨勢看,還是從金融企業混業經營、金融企業投資實體企業的特點看,産融結合都是大勢所趨。例如國家電網、寶鋼公司投資參股建設銀行,中投公司投資保利協鑫和海外石油項目,首鋼集團控股華夏銀行等。”
因此,他認為,國有資産“家底”在此情況下難以準确摸清。一旦出現資産流失等問題,誰應該對國有資産負責任。
針對《意見》中提出的“各類國有資産進行專項彙報”,劉紀鵬将其看作是回避矛盾的表現。他說,“是繼續各個管理部門分别進行彙報,還是從組織架構上由專門部門統一做報告,意味着現實中責權利的再劃分。而這才是改革的關鍵。”
從科學分工、責權利相統一的角度出發,他建議改革應參照《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管資本為主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産集中統一監管,并集中由一個部門統一報告。
如何破解科學分工、統一責權利的改革難題,中國特色的國資監管模式中蘊藏答案。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始終有一個困惑,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别,能否走出中國模式”,劉紀鵬說,“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征是實現市場經濟的宏觀運行機制和中國公有制背景下的運行載體的創新性結合,結合點就在國有資本和市場經濟之間。”
其中,國有資産分類和管理問題這兩個環節,最為重要且複雜。
中國有着龐大的國有資産規模,可分為金融、産業、行政性、自然資源等。劉紀鵬表示,“就國有資産分類而言,行政性、自然資源這類非經營性國有資産依靠公共預算,與西方經濟體制并無差異。而經營性國有資産,才是中國模式的基本特征。”
自2004年參與《企業國有資産法》起草,劉紀鵬所在的專家組遇到的首個難題就是國有資産分類。面對四類國有資産,是立一部涵蓋所有類型的大法,還是解決經營性國有資産這個當務之急,成為一大争議點。當時為了抓主要矛盾,力堵國資流失“黑洞”,僅針對經營性國有資産立了一部“小法”,這為今天留下了進一步的改革空間。
針對歸誰管的問題,劉紀鵬提出了當前條塊式監管的弊端。他表示,目前,國資監管機構主要負責非金融類企業國有資産的監管,财政部門主要負責金融類企業國有資産、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産的監管。從所有者角度看,這種劃分有一定道理,但由于我國國有資産存量巨大,财政部作為公共管理部門,卻去履行金融國有資本出資人的職責,在體制上不順。
改革還是要解決資本的所有者問題。為此,劉紀鵬提出理論、立法先行,重點就是解決政府之間的分工。首先,成立一部國有資産“大法”。其次,分設兩個部門。一是經營性國資委,二是建立資源性國資委。行政性、公益性等非經營性國有資産納入公共預算,劃歸财政部。
立法先行、科學分工、責權一緻,如此一來國有資産底數不清、監督不力等問題可得以根本解決。
在劉紀鵬看來,中國模式核心是實現國有資本和市場經濟的結合。國資監管部門在大法的思路下科學分工,勇于自我革命。沿着這一思路,才能抓住中國模式的要旨和靈魂。